斗神传说 一
瓦当里有座破败的草屋,孤伶伶地立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苍凉无比。我猜想,屋子里一定也会有一个同样迟暮的老人,他们为世人所遗忘,已经不起任何风雨。我的伤口隐隐作痛。我伸出手去,试着推开了那扇紧闭的门,眼前的一切令我目瞪口呆。满屋子的兵器寒光四射,一位老人在一座巨大的熔炉前捧着一把剑
瓦当里有座破败的草屋,孤伶伶地立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苍凉无比。我猜想,屋子里一定也会有一个同样迟暮的老人,他们为世人所遗忘,已经不起任何风雨。我的伤口隐隐作痛。我伸出手去,试着推开了那扇紧闭的门,眼前的一切令我目瞪口呆。满屋子的兵器寒光四射,一位老人在一座巨大的熔炉前捧着一把剑,神情专注,就像一位母亲手里捧着刚出世的孩子。看着那些兵器,我突然有了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老人是一位铸剑师,他给我讲述了关于兵器的许多传说,那是一些关于战争的情节,在老人平静的语气中,它们在我脑海中迅速铺成一幕血腥场面,让我强烈地感到恐惧,同时又无比向往。隔着这些冰冷的兵器以及兵器背后的传说,我的目光穿透了老人的一生。回来后,总有一些刀光剑影在我眼前飞舞,黄昏的时候,我找了段木头坐在村口削成斧。斧削成了,沉沉的,
握在手里头有种踏实的感觉,我发现自己十指修长,木柄斧在手中姿态优美,也许我天生就适合握斧。
刀剑历55年!我又一次去了铸剑师的屋子,看那些挂在墙上形状各异的兵器,它们在黑暗的屋子里闪着冰冷的光泽,这种光泽一触到我身上,我便热血沸腾。老人坐在熔炉前,炉火使他目光明亮,我看到他的背影在明灭的火光下跳跃,就像挂在屋外那面迎风招展的幌子,上面醒目地写着----“兵器”两个字。
我的目光贪婪地在铸剑师的屋子里四处游走,最终定格在一把通体黝黑的斧上面再也无法移开。它静静地躺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光辉暗淡 ,这种光辉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跪下来对着它顶礼膜拜。我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走到那它面前,就像一名虔诚的朝圣者走向他心中的圣地。我跪了下来,将脸贴在斧面上,它散发出冰冷刺骨的寒气,似乎轻易就穿透了我的头颅,将我的思维冻结在它所拥有的神秘力量里。我仿佛看到无数的亡魂镶在这件神秘的兵器里,他们呼天喊地穿冗长的历史而来,将一张张血肉模糊的面孔摆在我面前,告诉我这把摆在我面前令我迷乱的兵器叫做---镇恶。
我轻轻一挥手,镇恶就蹦了起来,我紧紧地把它握在了手里,心情激动得就像握住一些生死攸关的命运。铸剑师在后面睁着惊恐的眼睛看我,他那张原本苍老的脸在熔炉前突然间变得生动无比,就像那些原本锈迹斑斑的废铁,经他的手摇身一变成了寒光四射的兵器一样,闪着动人的光泽。我想,他的生命已经融入了这把叫镇恶的兵器里。
我告诉铸剑师:“镇恶现在是我的了,镇恶是为我而生”。
铸剑师回答我:“镇恶现在是你的了,你是为镇恶而生”。
五百年了,瓦当镇还没有人能拿得起这把镇恶。铸剑师走出草屋,头也不回的消失在瓦当镇如血的夕阳里。
铸剑师走后,屋子里的东西他一样也没带走,兵器还是那么整齐地挂满在四周墙壁上,那座燃烧了几百年的熔炉也还在一如既往地窜着火苗。再细看的时候,我却发现那些兵器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颜色,它们倦倦地贴在墙壁上,像一些被风干了的蛇一样了无生气。其实,铸剑师已经带走了属于他的一切----那些兵器的灵魂。
走出屋子,我看到几朵红色的云挂在天边燃烧,天空看上去就像铸剑师屋子里的那座熔炉。我想,铸剑师一定将火种带去了那遥远的天边。
我把镇恶背在背上,听见铸剑师的屋子在我身后开始清晰地崩蹋,分崩离析的声音将我的耳膜撞得嗡嗡作响。我回过头去,看到刻着兵器两个字的幌子在漫天的尘土里飞扬着席卷了天边的夕阳。
世界岿然不动,而生命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那一刻我无比清醒,我想到了时间。到瓦当镇后,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我无法从那些日升日落的天空里看到一丝丝四季交替的痕迹。我相信时间是静止的,在静止的时间里我看到许多记忆从我脑海里飞驰而过,奔向心脏。
一道闪电从天空划过,像八爪鱼一样在天空张开了枝枝丫丫的臂膀,接着便有雷声在云层里轰隆隆地滚动。我抬起头来看到白色的云朵像雪花一样飘浮在清澈明亮的天边。这样如洗的天空,难道暴风雨会来临吗?我苦苦思索但又很快放弃,这一路上的奔波,使我习惯了对着风雨微笑。
地势越来越窄,两边的山呈八字形轨迹渐渐向小路挤压着,将前面不远的地方出一道口子来,山势在口子处陡然止住,这就是去洛阳城谷口了?
我走出谷口,天地豁然开朗,一幅画面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一样袭击了我:一个衣着华丽的男子站在离谷口百步的地方,修长削瘦的身影在阳光下顶天立地,风吹起了他的头发,我看到一张满是血污的脸在满头乱发中时隐时现。他每一举手,每一投足,都会有一种美丽的魔法从他身上发出。冰,火,天雷不停地向谷里的两只猪妖奔涌而去,将这一方天空映得绚丽无比。
握在手里头有种踏实的感觉,我发现自己十指修长,木柄斧在手中姿态优美,也许我天生就适合握斧。
刀剑历55年!我又一次去了铸剑师的屋子,看那些挂在墙上形状各异的兵器,它们在黑暗的屋子里闪着冰冷的光泽,这种光泽一触到我身上,我便热血沸腾。老人坐在熔炉前,炉火使他目光明亮,我看到他的背影在明灭的火光下跳跃,就像挂在屋外那面迎风招展的幌子,上面醒目地写着----“兵器”两个字。
我的目光贪婪地在铸剑师的屋子里四处游走,最终定格在一把通体黝黑的斧上面再也无法移开。它静静地躺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光辉暗淡 ,这种光辉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跪下来对着它顶礼膜拜。我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走到那它面前,就像一名虔诚的朝圣者走向他心中的圣地。我跪了下来,将脸贴在斧面上,它散发出冰冷刺骨的寒气,似乎轻易就穿透了我的头颅,将我的思维冻结在它所拥有的神秘力量里。我仿佛看到无数的亡魂镶在这件神秘的兵器里,他们呼天喊地穿冗长的历史而来,将一张张血肉模糊的面孔摆在我面前,告诉我这把摆在我面前令我迷乱的兵器叫做---镇恶。
我轻轻一挥手,镇恶就蹦了起来,我紧紧地把它握在了手里,心情激动得就像握住一些生死攸关的命运。铸剑师在后面睁着惊恐的眼睛看我,他那张原本苍老的脸在熔炉前突然间变得生动无比,就像那些原本锈迹斑斑的废铁,经他的手摇身一变成了寒光四射的兵器一样,闪着动人的光泽。我想,他的生命已经融入了这把叫镇恶的兵器里。
我告诉铸剑师:“镇恶现在是我的了,镇恶是为我而生”。
铸剑师回答我:“镇恶现在是你的了,你是为镇恶而生”。
五百年了,瓦当镇还没有人能拿得起这把镇恶。铸剑师走出草屋,头也不回的消失在瓦当镇如血的夕阳里。
铸剑师走后,屋子里的东西他一样也没带走,兵器还是那么整齐地挂满在四周墙壁上,那座燃烧了几百年的熔炉也还在一如既往地窜着火苗。再细看的时候,我却发现那些兵器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颜色,它们倦倦地贴在墙壁上,像一些被风干了的蛇一样了无生气。其实,铸剑师已经带走了属于他的一切----那些兵器的灵魂。
走出屋子,我看到几朵红色的云挂在天边燃烧,天空看上去就像铸剑师屋子里的那座熔炉。我想,铸剑师一定将火种带去了那遥远的天边。
我把镇恶背在背上,听见铸剑师的屋子在我身后开始清晰地崩蹋,分崩离析的声音将我的耳膜撞得嗡嗡作响。我回过头去,看到刻着兵器两个字的幌子在漫天的尘土里飞扬着席卷了天边的夕阳。
世界岿然不动,而生命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那一刻我无比清醒,我想到了时间。到瓦当镇后,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我无法从那些日升日落的天空里看到一丝丝四季交替的痕迹。我相信时间是静止的,在静止的时间里我看到许多记忆从我脑海里飞驰而过,奔向心脏。
一道闪电从天空划过,像八爪鱼一样在天空张开了枝枝丫丫的臂膀,接着便有雷声在云层里轰隆隆地滚动。我抬起头来看到白色的云朵像雪花一样飘浮在清澈明亮的天边。这样如洗的天空,难道暴风雨会来临吗?我苦苦思索但又很快放弃,这一路上的奔波,使我习惯了对着风雨微笑。
地势越来越窄,两边的山呈八字形轨迹渐渐向小路挤压着,将前面不远的地方出一道口子来,山势在口子处陡然止住,这就是去洛阳城谷口了?
我走出谷口,天地豁然开朗,一幅画面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一样袭击了我:一个衣着华丽的男子站在离谷口百步的地方,修长削瘦的身影在阳光下顶天立地,风吹起了他的头发,我看到一张满是血污的脸在满头乱发中时隐时现。他每一举手,每一投足,都会有一种美丽的魔法从他身上发出。冰,火,天雷不停地向谷里的两只猪妖奔涌而去,将这一方天空映得绚丽无比。
与 斗神传说 相关的文章有:
- 斗神传说 二 (2005-1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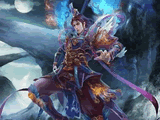 刀剑资料片枪将决专题
刀剑资料片枪将决专题 刀剑英雄地图攻略
刀剑英雄地图攻略 刀剑英雄任务大全
刀剑英雄任务大全